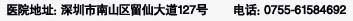本文是作者投来的稿件,编辑看完拍案叫绝,太深刻了。产妇死亡事件本是探讨医疗制度、医患关系的机会,结果变成了对媒体的道德审判。这样的结果是,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被削弱,而实实在在的社会矛盾被转嫁了出去。这种操控舆论的行为真的很可耻。本文是三十立铺独家稿件,欢迎转发,禁止转载。
文/夏颖
近期,一则“湘潭一产妇剖腹产后大出血不幸离世”的新闻成了轰动整个互联网的话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舆论战。这原本是探讨紧张的医患关系、备受争议的医疗制度、社会伦理与医药科学的冲突等问题的绝好机会,但舆论的导向却因凤凰评论员唐驳虎等人的引导,莫名转向指责媒体报道不当、媒体伦理与职业素养的缺失等。
这种舆论导向的方向从“监督政府”转向“监督媒体”,对媒体的社会监督能力将是致命打击。因此,作为媒体人,笔者有必要用新闻常识,结合那篇有争议的报道,澄清下这个问题。不然,这种舆论导向贻害无穷。
新闻记者的职责是什么
新闻记者最重要的职责是为公众“报道新闻事实”。李普曼提出,大众不再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客观环境,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去认知世界,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实质上是媒体构建的虚拟空间。
那么这个媒体所构建的“虚拟空间”到底有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我们真实的世界,这就取决于媒体大多大程度上“真实报道”客观事实。
这也是对新闻记者最高的职业要求:尽可能真实准确的反映事实发展的全貌。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才是真实报道?我们都知道,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剪辑会让新闻事实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这世界上永远没有绝对的真。在这样的哲学前提下,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个人视角的切入和观点的呈现会给新闻事实本身带来影响,西方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尽可能陈述新闻事实,避免对事实进行评论”,目的就是要去除任何主观性视角地加入对新闻事实的损害。对新闻事实的评判的权力应该交给观众,记者所需要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还原新闻事实。
产妇死亡报道并未失实
“产妇手术台死亡,医生齐失踪”这篇报道之所以引发了大规模的舆论声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篇中的一段话“妻子赤身裸体地躺在手术台,满口鲜血,眼睛里还含着泪水,可却没有了呼吸。而本应在抢救的医生和护士,却全体失踪了,房间里只有一些不明身份的男士吃着槟榔,抽着烟。”
回顾整篇报道,在“何时,何处,何地,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的新闻五要素上,这篇报道可以说是事实明确,陈述适当,不存在故意地夸大和不实报道。虽然标题“医者齐失踪”这样的字眼确实有着吸引眼球,追求轰动效应的嫌疑,但这一事实结论是建立在陈述事实的基础上的。
至于“医生没有出现在手术台,而是呆在了休息室”这算不算失踪这样的问题,医院的规章制度,我国的医疗法中寻找答案,已经不是记者在这篇紧追第一时间报道的新闻中需要陈述的。
唐驳虎的指责无理
在对这篇报道的批评指责中,唐驳虎在文章中指责记者没有向观众解释“羊水栓塞”这一医学难题对救助患者产生的危险,没有向观众解释针对这种病案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才是合理的。
不可否认地是,对引发这个病例的根本性原因“羊水栓塞”确实需要进行适当地解释,但是这绝不是这篇报道的致命错误。在采写新闻中,由于需要满足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实的市场需求,记者新闻事实的初期报道中确实会存在一定的事实模糊,但完全可以在后续的报道中进行补充与说明。
我们要适当地原谅记者在这篇报道中存在着一定的疏忽与不足。特别是对这则报道来说,根本性问题并不在于“羊水栓塞”这一病例本身的危险性和致死率,也不在于医生什么样的治疗措施才是合理有效的,更不是解释是由于患者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才导致的延误救助时机(如果确实存在这种问题)。
这些都不是重点,激发民愤地重点是医生在患者死后没有表示出对生命的最起码的尊重!这种对生命的漠视与对他人悲伤的冷漠极大地伤害了处于弱势的患者的心理。医疗死亡事故确实可以有千百种原因,这是可以由解释来阐明的,但是对生命的尊重却是宇宙中不变的法则,是我们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与伦理标准。
而“医生齐失踪”的事实彻底打破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在社会道德尺度缺失的时候再遑论新闻职业道德那就太可笑与幼稚了!何况在这篇报道中确实不存在记者断章取义式的陈述事实,也不存在出于追求轰动效应而炒作报道!
专业知识绝非最重要素质
唐驳虎评论员在批评这篇报道中指责记者缺乏专业知识,认为记者应该具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他指出,由于记者缺乏专业知识,所以提出了“羊水栓塞为何没有事先检查出来?”这样的明显缺乏医学常识的质疑。但是,这种质疑难道真是错误的吗?专业知识真的是记者的必备素质与要求吗?那我们还是先回到这篇报道上。
首先来看下“羊水栓塞为何没有事先检查出来?”这个提问。在这篇报道中这个提问是记者以家属的口吻提出来的,并且在报道中加上了引号,原文是“刘先生对湘谭县妇幼保健院提出了诸多质疑:妻子产前检查一切正常,为什么死亡以后就说是羊水栓塞?在产后抢救过程中,为什么没有讲过?”
我们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以这句话来指责记者缺乏专业知识实在是可笑至极。首先这个质疑明显是记者引述的患者的问话,而不是记者本人的质疑。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医学人士,我相信,百分之九十的非专业人士都无法理解为何“羊水栓塞为何没有事先检查出来?”
记者在陈述新闻事实中,准确无误和充分完整地将给予事件双方陈述新闻事实的机会,并将这种当事人极具个人观点和视角的陈述用引述的方式加以呈现,这是完全符合新闻法制和职业道德的要求的。
我们在报道中看到记者不但陈述了患者的质疑,并给了另一涉事方——医院陈述新闻事实的机会。院方的回答是“现在不便介绍情况”。陈述事实完备,充分给予事实当事人双方合理的解释和观点陈述的机会,把事件的评判权完全交给观众,这哪一点不符合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
其次,记者应该具备了解“羊水栓塞不能事先检查出来”的专业知识吗?且不论这个质疑根本不是记者提出的,即使是记者提出的,那么记者是否应该明白“羊水栓塞为何没有事先检查出来?”
这样的专业医学知识。专业知识真的是记者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吗?是决定一篇报道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吗?关于这个问题,早期曾经在新闻教育实践上备受争议。一度我们提出了财经记者,金融记者,体育记者的分类培养的模式,认为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应该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的基本素质。
但是新闻教育的实践很快回答了这个问题,专业知识绝不是一名新闻记者的必备素质。简言之,新闻传媒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场地和学术领域,是由于它具备独属于传媒行业的职业要求和学术理论。
新闻从业者需要的能力
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从业者,一流的写作能力,出色的采访技巧,敏锐的新闻敏感,高尚的道德素养,才是必备素质。民国时期的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为勉励同仁,取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而被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改为“辣”,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京报报社墙上。
这四字也成了新闻从业者的最高的职业信仰与标准。而做为一介文人的他,为使政府听命于民意被军阀处死,临刑前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成了千古流芳的记者典范。
作为一名合格的新闻从业者,记世间冷暖,录民者之声,为弱者呼吁,为正义奋战,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在现代传媒社会,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域中,适当地专业知识,确实有助于记者报道新闻事业的准确性。
但是世间行业千万,要求记者在每次危机性报道和事故报道中都准确无误地解释专业知识,就是勉为其难。新闻震撼人心的力量绝不在于专业知识的普及,教育只是新闻的辅助功能,新闻的力量在于明辨是非、秉公记载,传承社会道义,发扬舆论利器功效,这才是记者最重要的职业要求。
莫把媒介审判变为审判媒介
“媒介审判”(trialby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具体到这篇报道,如果记者存在预设性观点,暗示或引导观众得出“医疗救助不当是引发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报道方式确实存在媒介审判。在“产妇死亡”报道中,唐驳虎指责记者不应该不具备基本的医学常识,而故意夸大其词,哗众取宠,断定医生没有履行基本的职业责任。
如果记者没有经过深入性调查,就推论出医疗事故的责任归属问题,将产妇死亡的原因完全归属于医疗救助不当,那么确实存在媒介审判的报道倾向。可翻遍报道,可以看到记者并没有对事故责任归属给出任何独断性地结论,实际上大众也同样没有独断地从这篇报道中得出“医生不当治疗才导致患者死亡”这样的结论,在上文已经说明医院处理这起医疗事故的态度而不是能力,罔顾生命的名医比治病害人的庸医更可怕。所以,以此来指责记者由于缺乏专业医学常识误导大众,无端制造社会不安与矛盾,才真正是断章取义,立场偏颇!
媒介审判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媒介引导大众舆论的作用,作为“第四势力”的媒体从业者由于过多的主观观点的渗入、经济利益的诱惑、博取眼球效应的动机,导致媒介报道错误地影响了观众认知事实真相的能力,影响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导致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出现了失衡。
早期的马加爵案件就是一起著名的媒介审判案例。其实在中国媒介审判只是个理想性词汇,由于中国的司法程序不同于西方,媒体报道实际上很难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充其量是扩大事件的社会影响,增强事件的舆论监督力量,使政治性话语与传媒话语、个人话语可以在一定层面上形成交流与碰撞,这其实从反面显示了中国媒介监督力量的强大,社会民主的进步,有助于引导社会主流观点的讨论,构建公正合理的社会道德体系。
近年来由于传媒力量的不断突显,特别是网络舆论监督的兴起,媒介审判的现象层出不穷,这正显示了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强大,如果将媒介审判改为审判媒介,这种矫枉过正的作法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批判媒体背后的逻辑
唐驳虎先生展开的针对这则“产妇死亡,医生护士齐失踪”报道的新闻媒介从业者道德抨击,对新闻记者的报道准则,叙事方式,职业道德要求存在着诸多误读。这种将矛头对准“监督政府”的媒体,转嫁真正的社会矛盾,这种方法势必将会对媒体的监督力量产生摧毁性的打击。
如果不明白基本的媒体报道的准则与方法,将会剥夺新闻记者手中仅有的报道事实的权力。如果没有媒体,那么民众会丧失基本的讨论事实、评判事实的权力。在这则报道中,我们更应该